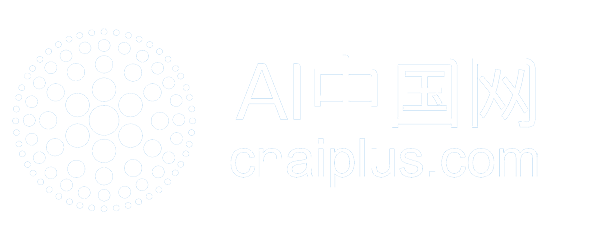AI中国网 h ttps://www.cnaiplus.com
Santiago Ramón y Cajal被认为是现代精神科学之父的西班牙组织学家和解剖学者,他也是一位心理学家,坚定地相信精神分析学和弗洛伊德学说关于梦的理论是「集体的谎言」。当弗洛伊德在1900年出版了《梦的解析》一书时,整个科学界都为他的潜意识理论所迷倒。梦境很快就成了被压制的欲望的同义词。精神分析学家认为,只要有正确的解析,令人迷乱的梦境可以用来解开被尘封的心结。 Cajal因发现了神经元的存在而获得1906年诺贝尔奖,更为著名的是,他靠直觉想出了神经元突触的形式和功能,打算证明弗洛伊德是错的。为了证明「所有梦境都是被压抑欲望的结果」这一理论是错误的,Cajal开始做梦境笔记并收集其他人的梦境,严苛并有逻辑的分析这些梦境。他的记录第一次被译成英语,而这些梦向人们展示了一位伟大科学家的内心世界。Cajal最终认为这项课题不宜出版,但在1934年去世之前,他把他的研究,潦草的写在彩色活页纸、书籍和报纸边缘上的这些东西,给了他的好友且曾是他学生的精神病学家José Germain Cebrián。Germain把他的日记打印成一本书,这本书曾被认为在1936年西班牙内战期间遗失了。实际上Germain把手稿一直带在身边周游欧洲各国。在 Germain去世前,他把手稿给了 José Rallo,一位西班牙精神病学家及梦境研究者。让学者和热衷者高兴的是,《Santiago Ramón y Cajal的梦》于2014年在西班牙出版了,其中包括Cajal在1918到1934年1月去世前记录的103个梦。 在此本书第一次被译成英文,这些梦还有Cajal的笔记,都向人们展示了这位伟大科学家的内心世界,可能连他自己都没注意到的内心世界。 [caption id="attachment_6626" align="aligncenter" width="733"]
 《这只是个梦》:Santiago Ramon y Cajal否认佛洛依德的梦境理论。Cajal相信梦只是一系列未经前额叶皮层过滤的随机图像,而大脑尝试理解这些图像。一些近期的梦境研究支持Cajal的理论。维基百科。[/caption]
Cajal称赞理性的思维和有意识的意愿。在他的自传中,这位科学家描述神经元是「神秘的灵魂之蝶,某天煽动它们的羽翼,谁知道呢,可能就能揭露精神生活的秘密。」他终生迷恋做梦和梦境,即使(或者也许是因为)其他人倾向于抵制所有合理的解释。在他职业生涯的早期,Cajal研究催眠和暗示的力量,为了那些歇斯底里,神经衰弱和灵魂媒介的人,他把他的家变成了一个诊所。并且,他计划出版三本心理学的书,之后判定书的内容太过推测:《关于催眠,唯心论和形而上学的论文》;《梦境:解释性教义的批判》;和《梦境》。然而,他确实在1908年发表了一篇关于做梦和视觉幻觉现象的科学论文,它的开头是「做梦是大脑生理机能最有趣且最奇妙的现象。」他在盲人中调查视觉幻觉现象,总结出视网膜在做梦期间是不活跃的,相反,确认了相关皮层,丘脑和胶质细胞是活跃的证据。
在1902年,通常内向的Cajal允许自己对梦境更自由地形成理论,在一本当代诗集的序言中,他写道,「大多数梦由思维碎片构成,毫无关联或者奇怪地组合在一起,这有点儿像是不成比例、不和谐或无厘头的荒谬怪兽。」他推断做梦发生在大脑皮层未使用的区域:「大脑的休眠区,也就是未被意识到的图像被记录的细胞,保持着清醒并变得兴奋,通过隐藏在有意识思维之后的练习使它们复苏。」在清醒一天的最后时刻,据Cajal说,某些特定的细胞群已经累坏了,在睡觉时留下别的群体去工作。比之于任何理论,这种持久的细胞聚焦说是Cajal留下的心理学遗产,现在它确实促进了神经生物学的研究方法。一些当代的关于做梦神经科学的理论,即激活-整合的假说,似乎支持 Cajal关于梦的说法,认为梦只是一系列未经前额叶皮层过滤的随机图像,而大脑尝试理解这些图像。
Cajal关于梦的解剖式的观点以及他不愿进行没有生理证据的推测,这与弗洛伊德梦的理论形成了鲜明对比。在一封于1935年出版的写给Juan Paulis的信中,Cajal写道,「除了一些极其罕见的情形,不可能核实教条的确切性和那些自负的维也纳作者,他们似乎总是更专注于建立一个耸人听闻的理论,而不是渴望找出科学理论的起因。」
像许多神话天才一样,Cajal更献身于他的事业而非他的家庭。Cajal沉迷于他的显微镜中,无法回应他的妻子Silveria Fañanás García,那时她尖叫着度过了6岁女儿死去的夜晚。在哀嚎中,显微镜的灯光是Cajal唯一的避难所。在女儿死后的三十年,这位当代神经科学之父梦到他正溺水于西班牙海岸,把他的小女儿紧紧搂在怀里。这个梦不需要进一步的剖析。
以下记录的手稿中, [—— ] 表明,在他最初的笔记中,Cajal留下了空白;* * *表明此处他删去了一些东西。
《这只是个梦》:Santiago Ramon y Cajal否认佛洛依德的梦境理论。Cajal相信梦只是一系列未经前额叶皮层过滤的随机图像,而大脑尝试理解这些图像。一些近期的梦境研究支持Cajal的理论。维基百科。[/caption]
Cajal称赞理性的思维和有意识的意愿。在他的自传中,这位科学家描述神经元是「神秘的灵魂之蝶,某天煽动它们的羽翼,谁知道呢,可能就能揭露精神生活的秘密。」他终生迷恋做梦和梦境,即使(或者也许是因为)其他人倾向于抵制所有合理的解释。在他职业生涯的早期,Cajal研究催眠和暗示的力量,为了那些歇斯底里,神经衰弱和灵魂媒介的人,他把他的家变成了一个诊所。并且,他计划出版三本心理学的书,之后判定书的内容太过推测:《关于催眠,唯心论和形而上学的论文》;《梦境:解释性教义的批判》;和《梦境》。然而,他确实在1908年发表了一篇关于做梦和视觉幻觉现象的科学论文,它的开头是「做梦是大脑生理机能最有趣且最奇妙的现象。」他在盲人中调查视觉幻觉现象,总结出视网膜在做梦期间是不活跃的,相反,确认了相关皮层,丘脑和胶质细胞是活跃的证据。
在1902年,通常内向的Cajal允许自己对梦境更自由地形成理论,在一本当代诗集的序言中,他写道,「大多数梦由思维碎片构成,毫无关联或者奇怪地组合在一起,这有点儿像是不成比例、不和谐或无厘头的荒谬怪兽。」他推断做梦发生在大脑皮层未使用的区域:「大脑的休眠区,也就是未被意识到的图像被记录的细胞,保持着清醒并变得兴奋,通过隐藏在有意识思维之后的练习使它们复苏。」在清醒一天的最后时刻,据Cajal说,某些特定的细胞群已经累坏了,在睡觉时留下别的群体去工作。比之于任何理论,这种持久的细胞聚焦说是Cajal留下的心理学遗产,现在它确实促进了神经生物学的研究方法。一些当代的关于做梦神经科学的理论,即激活-整合的假说,似乎支持 Cajal关于梦的说法,认为梦只是一系列未经前额叶皮层过滤的随机图像,而大脑尝试理解这些图像。
Cajal关于梦的解剖式的观点以及他不愿进行没有生理证据的推测,这与弗洛伊德梦的理论形成了鲜明对比。在一封于1935年出版的写给Juan Paulis的信中,Cajal写道,「除了一些极其罕见的情形,不可能核实教条的确切性和那些自负的维也纳作者,他们似乎总是更专注于建立一个耸人听闻的理论,而不是渴望找出科学理论的起因。」
像许多神话天才一样,Cajal更献身于他的事业而非他的家庭。Cajal沉迷于他的显微镜中,无法回应他的妻子Silveria Fañanás García,那时她尖叫着度过了6岁女儿死去的夜晚。在哀嚎中,显微镜的灯光是Cajal唯一的避难所。在女儿死后的三十年,这位当代神经科学之父梦到他正溺水于西班牙海岸,把他的小女儿紧紧搂在怀里。这个梦不需要进一步的剖析。
以下记录的手稿中, [—— ] 表明,在他最初的笔记中,Cajal留下了空白;* * *表明此处他删去了一些东西。
一个普通的梦
[裤子掉了] 我参加了一个外交晚会,晚会后把裤子落在了那。(这是我的欲望吗?) [和女儿一起落水了] 我在岸边散步(大概是在桑坦德),结果我抱着小女儿落了水。我划水,我挣扎,但就是抓不到海岸边上。后来,这个噩梦惊醒了我。
晨梦
[人性宣言] 1926年12月12日 我梦见在讲课,讲什么是哲学学科。之后我发现自己周围都是朋友,不知怎的,谈论起一个问题:构成人性的是什么?我以一种权威地声调要求别人不准说话并抓住了所有听众的注意力——所有的朋友和同事——(我听见了自己激烈宣布的声音),我宣称人类个体的统一教条[——]是一种错觉,我认为现实中有四种人在我们的内心深处:- 石头人,细胞的尸体,结缔组织,骨骼 * * *,细胞间物质X,它是生命的填充物,构成有强度的身体,就像建筑的石膏。
- 有腺体和情感的人,意思是指我们内部或者外部的分泌器官,由* * * 交感神经节调节,掌管植物性生命,控制更高层的个体(情绪和感觉)以及石头人。
- 有传播和有意识的人,意思是指大脑的神经系统,存放我们感觉残留物的地方。通过感官与外部世界相连,用某些脑通道连接至高层的自我。这种自我可以是有意识的(包括感觉,知觉),但它一般仍然作为基本思想(即很多学者所说的「潜意识」)的存储空间。它产生出反射或直觉时刻。更高级的自我由此变得活跃,专横,有意识的冲动。通过选择脑内储存的这些咨询文件[——]等途径,由此决定有用的明确的反应;参与,或不参与感知;抑制反射作用,压制本能,通过改变思维的感官物质来伪造思想和理论。这种自我是严格的自我,能看见却不被看见,是处于梦境中幻觉性狂欢的第二自我,会充满矛盾地说:够了,这一切都是幻觉,快醒来。相信它是自我的表现,就好像是在审视一个摄影镜头前的自己。如果有面镜子的话就很有可能了。可惜在人类中,自我没有那扇对应的镜子。自我是绝对无法进入的。所以我们在思想里创造了这面镜子,自我意识,它只显示出被我们[——]选择的东西 ,被认为是对象。但被当做对象的并不是我们所认为的那样,它其实只是意识里一部分图像…自我是一种能量,像看不见的神灵一般…

印刷媒体的梦
[有关重生的书的校样] 我发现自己在打印机旁校正一本关于重生的书的复本。我发现里面丢失了很多字母,缺少介词,语句从一行窜到另一行。我被这些错误震惊了,感到羞耻。 前后矛盾。我并不是在印刷过程中校样,而是一本已经印刷好的,等待出售的书,并且已经翻译成了英语。我的校正因此没有意义。还有,这本书,我不想再印刷一个新版本的书,是12年前就印刷的了。我醒来。 在检查错误中我所感觉的令人窒息的炙热导致了我的头剧烈地疼痛,现在已经无可避免。我在哈卡。 弗洛伊德解释不了这个。 这里什么也没有,只有之前扭曲的动作带来的回忆。 我想象着我正在Pueyo出版社,而这本书根本就没有被制作出来。新的前后矛盾。
梦境(在西贡萨)
[骨学课] 我是一个助教。忽然我在最后一分钟从院长那里收到了一个要求,来教学生们骨学。当检查这些记忆中的骨头时不安、愤怒 * * *。我列举了手部的骨头:手舟骨、头状骨,然后我不知道其他的了。同时整个班级等待着我,学生们大叫着。我问我自己我该如何继续讲述,在我已经几乎忘光了这些骨头的时候?愈加愤怒,我醒过来,伴随着如释重负的感觉,意识到我不是一个教授,我老了,没有人可以指挥我。 前后矛盾:- 独裁的决定,让一个77岁的退休老人教骨学。 2.我没有想出任何身体不适或时间紧迫无法备课的理由。 3.忘记了我知道的事情;当我醒来,我重新回忆了腕骨和跗骨的内容,没有任何错误。 (记忆中心的阻碍)
白日梦
1929年5月29日 在佛罗那和3:30以前 走快点。事情发生在剧院大厅吗? 我走进大厅,很明显,自由派和反对派在这里发生过争斗。走进大厅之前, 在一个类似休息室的地方,我看到各种受伤的人处于其他那些夸耀自己前额子弹伤口的人之间,Lafora边走边说,我有个严重的伤口。他没有绑绷带。我毫无武装地走进这个大厅,可以听到枪击声。一些敌人看见了我,但他们没有从我站的这边向我射击。另一边的一些人说:快走,这样就不会有事了。我非常狂妄地答道,随便你射,撑死也不过是砍掉我几个月的生命。但他们没有射击。 他们说不值得如此大动干戈。于是我走了。强烈的情绪让我从梦中醒来。 这看上去更像是射击演习而非真正的战役。没有什么事情强迫我参与进去。似乎这场斗争只是政治性的,仅处于自由派和反对派之间的。 完全扯淡。我没看到任何死人。 原因:今天早些时候读到有关Enrique de Mesa(译者注:西班牙诗人)死于脑梗的消息。我无法理解,为什么要处决那个试图杀害Valdemoros(芬兰人?)的学生。我没有和任何人聊过这个问题。那天白天,我的行为一直很平和;还开车去果园摘了些酸樱桃。 费解。我在读一本Julio Camba的书 [——]时睡着了。我没有看到任何被压抑欲望的信号。外孙女
一屋子野生动物。它们吃了她。我不活了。 彪形大汉不得不穿过田野,在他经过时,他拽住你的头,咬下去,之后他把头藏在一个枕头之下。 一个女孩在玩,他们猛推了她一把,她从陡坡上掉下来。吓了她一跳。 她撕碎了一个非常漂亮的洋娃娃的头,并用一个她画了眼睛和嘴巴的布娃娃的头代替。丑爆了,但她更喜欢。 小偷破门而入。我说:不要杀我。他们拿出一把左轮手枪,但之后发现只不过是个用来吓我的玩具。 在学校,书桌变成了床,你睡在上面。参观者进来给了你食物。老师给他们带来巧克力。 食人族。你在一个岛上,一些黑人食人族跳出来,把你放在烤架上,往你身上泼上油。而你如此平静。他们吃掉了你并报告说肉太硬了,应该更肥一点。 一个电影剧院在一家教堂里。一束光穿透屋顶,我能看到头骨和骨架。忽略更多吧。电影剧院居然是祭司的事。噩梦—触觉之梦 (Espronceda之夜)
[手中的大脑] 我梦见他们剔除了我的头骨,仅留一层包住大脑的皮肤。我能感觉到大脑和皮肤的接触并且大脑的重量往一边倾倒,我用手接住,等着医生给我做个保护帽。我认为他们剔除我的头骨是非常自然的,我还想起另一个同样的梦,在那个梦里头骨长了回来,顶部还得到了加固。我不理解这个手术,但却认为做这些非常正常,而大脑就是仅覆盖一层皮肤,不需要进一步防护。我在屋子里走了一圈,看到大脑掉出来时吓到了并因此惊醒。(这一幕发生在Zaragoza医院所在的大街上其中一间房子里)。我的* * *妻子也被吓到了。 (我其他时候梦到过这些)。惊讶的是能够走路并且不跌倒。我的手放在脑袋上,摸到了一些移动的平滑的东西。我警告我的妻子,她不知道有什么在我身上。我想念我那被抛弃的头骨。这是个我认为平常且自然的手术。最终我愤怒地醒来。我想尝试着去碰触,但在我清醒之前无法够到任何东西。 前因,验尸时看到过大脑?我不认为我过去几年曾看到过颅骨钻孔(是在Esproceda的头骨上吗?)这儿不可能是视网膜理论。 这些是情感的梦境,它们无需解释。它们使我立即醒了过来。梦境
与工程师夫人一起用餐 我应邀来到工程师的家。他夫人看我吃得很欢实。她显得很惊讶,接着恭喜我,因为之前她听说我病了,还在节食,每天吃得很少。我们谈起她丈夫,一所学校的职员,但我并不认识他。谈到那些我并不认识的职员的勾心斗角时,我明智地说:抱歉,我几乎不认识土木工程学院的教授。 矛盾的地方:我好些年没在外面吃过饭了。我不认识好到会邀我去他们家吃的工程师的夫人。 但是,有人会说,V.病了,V.经常没食欲。吃好点,V.,所以他的梦满足了食欲。 但是,我的梦没有一丝[一一]弗洛依徳能够解释的地方。剩下的,让人痛苦的那些?我们是否应该求诸无意识的记忆?但是,这就摧毁了弗洛伊德的假设。无论它们是否从过去来到这些让人痛苦的场景,任何欲望都未在此获得满足。为了从一百个梦中发现八十个梦的潜在欲望,人就不得不变得非常不动声色,似是而非。 其他时候,我授课或开会。 欲望?没有。欲望在工作中,更在我的处境中。这个养成的习惯已经被放弃五年了。还有继续保持下去的欲望?没有。 但是,即使这是真的,应该还是符合我的假设。倾向于这一任务的大脑细胞正在休息,它们充斥着太多感官的、运动的、理想化记忆,过度刺激减轻了它们的负担。让我们记住这些完美逻辑的商讨。 选自nautilus,作者BEN EHRLICH,编译出品。参与:salmoner,20e,Fm018-庞,Chen Xiaoqing,微胖,柒柒。AI中国网 h ttps://www.cnaiplus.com
本文网址: